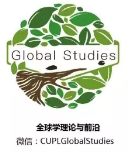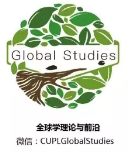各位同仁、朋友:
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拙著《拓开天外无穷景:一个全球主义者的学术人生》的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我的家人,朋友,学生以及学界同仁的鼓励,特别是得到了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王康社长策划了学术人生丛书,我的拙著有幸成为这个丛书的第一本著作。该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而是我对个人四十年学术生涯的追忆、梳理与审视,总结了我学术生涯的三大阶段和学术旨趣,阐述了我在交叉性,边缘性,整合性中探寻理论突破点的学术主张与观点。
关于我的这本拙著,谈两点意见与大家交流、分享。
第一点,关注并探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
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关注并探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什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不分国家、民族、种族,地区,整个人类都认同并践行的共同规则、理念与价值。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平、发展、幸福都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理论与价值。尽管人类在不同的时代、地区、国家、民族以不同的方式、途径、传统、偏好、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展示着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但不要忘记正是在这种多彩生活的背后,不断生成和凝聚起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它们是人类共同追求与奋斗的结晶,规范和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立足于共同性的视角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如在《契约论研究》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政体学说》两本专著中强调:政治无疑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我们通常的习惯性认知。但政治现象、政治生活中还存在共同性,这却是以往我们忽视甚至批判的,这种认知应该改变。像西方政治思想思想史中的契约论就包含着主权在民、人道主义观念、契约观念等共同性价值与理念。而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政体学说更是肯定了共和制、代议制、选举制是人类政治制度建设的一种共同选择,这些都彰显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共同性。进入90年代后,我的学术旨趣转向全球问题、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性等议题,它们都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并意味着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共同的价值,这一切都体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要求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视野,那就是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种共同性、全球性的理念与价值,已在人类生活中开始得到更多的认同与践行,而我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旨趣恰恰与时代的发展契合。经过近30年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沉淀,从2011年开始我着手全球学学科的建设,这是我一生的夙愿,也是为了完成1994年赵宝煦先生为我的《当代全球问题》一书作序时的嘱托。经过努力,2012年我们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获批全球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这表明在借鉴国际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全球学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全球学学科。随后又于2014年推出专著《全球学导论》,该书入选当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又由英国著名的劳特里奇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了英文版。《全球学导论》在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观上力求做出突破,整部著作围绕全球这一中心展开,突出全球性这一灵魂,从而与人们所熟悉并认同的立足于国家与民族观察、思考、处理社会生活的思维方法、原则、价值区分开来。也与人们在方法论国家主义框架下学习、认知和构建知识的传统路径与框架相区别。总之,可以说《全球学导论》,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研究的一次系统性梳理和概括,一种学理性探究与分析,它体现并上升到学科的自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在中国开展全球学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全面推进全球学学科的发展。
这种学科的自觉和学理的挖掘并未止于全球学。从2014年开始,我又进行了两项工作,一个是与中央编译局、南开大学合作编写并出版了《全球治理概论》教材,另一个则是申报并主持国家和北京市两项世界主义思想研究课题。在全球学研究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全球学所探究的全球性以及全球主义的理念、价值,与思想史、文化史,乃至宗教史上所出现的共同性理念与价值到底有何关系?全球学所依托的现实基础无疑是当下展现的全球化时代,而几千年人类历史中尽管不存在全球相互依存的事实,但却存在和出现过一些先哲和贤人对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的论述与向往。这些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关于共同性的观点,哪怕很零碎,很片面,但毕竟对当代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有启发、借鉴意义。所以从学术思想史上去系统地挖掘、梳理从古至今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的思想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历史上出现的关于人类社会中共同性的探究,正是学术界中已存在的世界主义思想。但迄今为止,世界主义思想往往都被视为一种过于理想的学说,在学术界处于边缘的被忽视的地位。我则认为,全球学所倡导的全球性、全球主义是历史上世界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当代表现,研究世界主义有助于从学术史、思想史上夯实全球学学科的学理基础。鉴于这种认知,我于2015和2016年分别申报并获批了两项世界主义研究项目,一项是北京市重大课题《世界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另一个是国家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史研究》。两个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五大板块系统研究世界主义思想。北京市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已于202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重大项目六卷本也于2023年呈送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在经历审读、审查过程,期待能于今年出版。
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的认知与研究,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知道,从理论和学术上讲,迄今为止认同并倡导这种共同性的,无论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都并非主流。此外,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始终是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中的共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本土性的关系,依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尽管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这轮全球化经历过上行、鼎盛的发展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也一度成为显学,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起,相继出现欧洲难民问题,三年新冠病毒疫情,直至当下的俄乌战争和特朗普主义,显学已经褪色退潮,学术界又重归现实主义。从现实和实践上看,地缘政治全面兴起,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全球生产、供应链受到脱钩的严重威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对二战后构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批判与抛弃,都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说不,似乎宣判着人类社会生活共同规则、理念与价值的死刑。
面对上述情况,我的观点是,从历史上的世界主义到当下的全球主义,人类对自身社会生活共同性的探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且在历史的进程中日益显示出更重要的份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否定、忽视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性、本土性。事实是,人类社会中的特殊性、本土性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共同性、普遍性的源泉。正是在多元的五彩的特殊性、本土性的发展和相互碰撞中,聚集和凝结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理念与价值。而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性、本土性在追求自身的自由发展和绽放自身的特殊文化时,又必然受制于人类认同的共同规则、理念与价值,不能背离人类文明的大道。显而易见,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本土性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我们要防止作茧自缚,从两个极端视角去思考和定位两者的关系。我愿意再一次引用拉兹洛的名言,“只看到差异性是老式的常识,只看到一致性也毫无意义。看到由进化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差异性中的一致性,或许是一种真正的辨识能力”。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于25年前提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概念,强调要尊重各国、各民族发展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自觉地以人类创造和凝聚起来的共同规则、理念与价值来观照自身的实践,寻求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共存与碰撞中的平衡。
至于当下世界发展的现实与未来走向,的确令人忧虑。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过时论、无用论甚嚣尘上。特朗主义不仅助长了全球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民粹主义主义的狂潮,并且力图摧毁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回到大国主导的丛林时代。总之,世界发展的图景,国际关系的生态无疑正在脱离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轨道,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新的历史周期正在显现。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大约三、四十年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具有巨变意义的时代。我们依旧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开端,它所标示的人类社会生活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并没有也难以从根本上被废除或终止,当下的贸易战和脱钩战已证明了这一点。而人工智能和人机共存所开启的颠覆性历史进程,为全球化时代增添了更深刻,更富有历史意义的内涵,它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将发生整体性变革,人类的共同规则、理念与价值将起到更大作用。
第二点,学者自身的主体性建设。
这里讲的主体性建设就是指学者的道德反省与伦理自觉。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学术界对研究主体自身素质与价值取向的忽视、麻木不仁是最大弊端之一,也是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自由思考,理性批判,尊重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这些基本的理念与价值似乎正在远离我们而去。浮躁,重形式,讲套话,唯上,唯项目,潜规则泛滥,对基本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背弃与冷漠,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它实质上反映了学术界令人忧虑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以及政治与道德的扭曲和缺失。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敢讲真话,愿意讲真话的学者越来越少,而溜须拍马,歌功颂德,假话套话连篇的学者则越来越得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一再强调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坚守两个基本理念,即学术执着与学术良知。学术的执着意味着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追求,不因任何功利的考量和各种困境而动摇、放弃。学术的良知,则意味着始终坚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批判精神,以人类的良心为座右铭,自觉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重任。针对当下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建设,我提出了四多四少的主张,即多些世界主义,少些国家主义;多些学术视角,少些政治偏好;多些独立人格,少些谋士情结;多些责任意识,少些功利考量。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主张全球化背景下的学者要有世界主义的视野与思维,理性审视并超越国家主义;要坚持客观的学理研究,抛弃政治偏好,意识形态偏好,阴谋论偏好;要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克服丧失自我,一心当谋士的追求;要有对人类,对文明负责的意识,摆脱和克服功利的诱惑。
概而言之,我的学术人生受到康德的影响。康德对其一生的总结与感悟是,要敬畏两种东西,即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对头顶星空的敬畏,使其一生从事世界与人类自身奥秘的学术研究。而对心中道德律的敬畏,则使其追求自由,诚实,善良,美,尽责,自律,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这两种东西也是我40年学术生涯的指南。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对我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
2025年9月20日